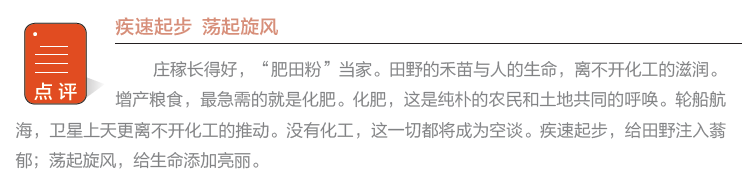- 最大
- 较大
- 默认
- 较小
- 最小
粮食问题引起中央的极大关注。中国氮肥工业艰难起步,在探索中冲刺。
“今后,我就向化工部要吃要穿了!”1961年4月,在杭州氮肥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化肥领导小组组长陈云半开玩笑地说。三年自然灾害,让国家粮食成了大问题。增产粮食,最急需的就是化肥。这不是玩笑,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化工部的领导深感责任重大。
历史性的杭州会议制定了发展化肥工业的方案,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成套设备问题,二是进口特殊材料问题,三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吴泾、衢州、广州三个“大”氮肥厂。一场化肥工业发展史上规模宏伟的大战役发出了总攻的号令。
再上吴泾
上海解放时,所谓的“两白一黑”就是白面、白米和煤炭紧张。当时毛主席提出,无论如何起码要有8个月的粮食储备。如今,在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充其量也不过只有几天的存粮。1961年春天,上海市委确定由市委常委李干成、生产委员会主任顾训方挂帅,组织全市大协作再上吴泾。
这里原是黄浦江中游一个偏僻的小镇。1958年,第一代建设大军举着红旗,唱着战歌开进了吴泾。漫卷的红旗映红了浦江水。没有公路,没有宿舍,小庙成了建设者最早的营房。国家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经济上遭受的重大挫折,使得吴泾的建设也受到影响。开工3年,只打了土建与硫酸工程几个前期战役,合成氨系统一直没有全面铺开。
杭州氮肥会议后,吴泾合成氨工程火爆起来。合成氨的“心脏”高压机水泥基础仍在连续浇灌。“不好,水泥用完了。”工地主任正嗷嗷叫着:“水泥,快,水泥!”这高压机立起来,好似一座小铁山,一个大飞轮就有两层楼房高。转起来,地动山摇,需要极牢固的基础。每个基础,包括牛腿支撑,要灌下去3000吨水泥,而且必须连续作业,一次浇完,决不允许中断。基础稍有差错,“心脏”就会出毛病,后果不堪设想。
材料员急得一屁股坐在冰冷的雪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工地指挥叼着哨子,唿扇着满是水泥点子的棉大衣,大踏步奔过来,一脚冲材料员屁股踹过去:“哭个屁,快叫人去运哪!”同刚下白班的工人,被工地主任的吼叫惊醒,睡意全消。这个鲤鱼打挺,那个鹞子翻身,像战士听到了冲锋号,奔出工棚。
刹时间,一道用百十号人的激情和意志拧成的水泥运输线搭起来了。水泥源源送上工地。工地主任尖厉的哨音一直响着,叫出了一轮新的太阳。1962年11月20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吴泾化工厂第一任厂长薛永辉,这位从抗日烽火中走出来的新四军太湖游击队司令,像当年接过革命火种要把抗日烽火点燃一样,郑重地点燃了第一根合成氨系统造气炉点火火炬,投进炉中去,投去了希望,投去了创业者积蓄多年的热情和力量。
火焰熊熊,原料气呼啸着钻入各自的管道,高压机铿锵鼓劲加压,合成塔不负使命,悉心将氮、氢拉在一起。晶莹、洁白的化肥,像珍珠,像银练,瀑布般倾泻下来,缓缓走入长长的运输带。我国自己设计、自已制造设备、自己组织生产出来的化肥,跃上史册。黄浦江水,波翻浪涌,一浪接一浪地拍击冮岸,哗哗哗哗,使劲地为创业者们的成功鼓掌、呐喊、祝贺。
主攻衢化
浙西重镇衢州北接江苏,西连江西,南挂福建,东扶上海,交通便利。衢化,就在这烂柯山下,千塘畈上。衢化筹备处主任刘德甫、党委书记孙文成,徒步行走十余里,到现场勘察厂址。
荒凉的干塘畈,一片烂冬田。有几个小青年远远地走过来,问:“听说,这儿建了大工厂,在哪儿呀?”“你看,那不是?”刘德甫手一指。“哪儿呀,就几间茅草屋。”“对喽,今天只有这几间茅草屋,明天就会变出合成塔、造气炉、大烟囱,管架如织,塔罐林立……”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卷起了沙尘,天骤然变脸,大雨哗哗下了起来。他们没带雨具,顿时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回到七八个人共同挤住的一间大屋,孙文成突然觉着肚子痛得厉害。阑尾炎,得手术。刚上阵就挨了一刀,孙文成心里感到窝火。躺在病床上,看刘得甫和副厂长张惠胜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手术还不到一星期,刀口还没长好,他就下床,奔了工地。
杭州氮肥会议开过,衢化本来就是毛主席点过头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掌上明珠如今成了全国化肥重点项目,更如顺水船,又加劲风吹,进度更快了。
深秋的一天,在一列风驰电掣的列车里,人们发现了一节特别的车厢。这本来是一节货车厢,却孤零零地载着一个“旅客”。顶秋风,冒冷雨,列车从辽宁锦西出发,向浙江衢州急驰。每到一站,这“特殊车厢”里便钻出一人,把件油渍麻花的大衣往身上一披,就连跑带颠地奔值班室,推门便讲;“我叫宋士悦,有件事请帮忙!”原来他是建设中的浙江第一座大化肥厂——衢化的押运员。车上押的是一台工地急需的造气炉。这可是化肥厂的龙头,早一天运到,就能早一天产出白花花的化肥。
于是,各站一律铺道放行。宋士悦是解放军炮校刚转业的准尉军官,分到衢化就被派到永利宁厂培训,中途接到北上催发造气炉的任务。这造气炉直径4米,长6米,重40吨,铁路称之为超限货,若是在哪个小站一耽搁,少则几十天,多则半年就甭动窝了。他一听这情况,就铁下一条心:“押车,我跟着,一定要让它人到货到!”他揣上几个窝窝头,披上唯一的一件旧军大衣,冒着北方初冬凛冽的严寒,钻进四面透风的造气炉。
四省两市十几个编组站,走走停停,1000多公里。别说洗脸、洗澡,有时连饮水也很困难。他凭着超人的毅力,拼过了孤独难耐的40个日日夜夜。到厂的时候,人们把他从造气炉膛里接出来。健壮魁悟的宋士悦,大衣里外虱子翻蛋,像个野人,头上都长了癞瘌。

衢化合成氨心脏高压机安装开始。省建筑安装公司张志岳小组承担主攻。高压机安装的精密度要求非常高,尤其是组装机身汽缸中心点,误差不得超过半根头发丝。安装时,一只汽缸只能容一个人侧卧里面,手拿千分尺,一头紧贴缸壁,一头与横在中间的细钢丝相碰,头戴耳机听声响,分辨倾斜度,而且必须连续操作,一间断就前功尽弃。这样冷的天,虽是南方,与冰铁块子拥抱也不是滋味儿,何况只能穿件卫生衣,几个小时下来,张志岳已是牙齿打架,咯嘣直响。
“师傅,吃饭吧!”“不行,不能让前边的功夫泡汤!送个窝头进来就行了!”突然,张志岳在里面喊起来:“糟糕,来尿了!”“师傅,出来吧,别憋坏了!”“不行啊,就差一节了,快给我找个家什!”“啥家什?”还是徒弟小王机灵,顺手从土建工地找出一根长竹筒,边往里送便喊:“师傅,顺这儿尿吧!”完活儿那天,张志岳收工两字还没喊出来,几个可爱的小伙子的眼皮说啥也吃不住劲了,都呼呼地到梦里庆功去了。
广氮热潮
1962春节,广州。化工部副部长昊亮平带领基建司的一位处长和设计院一位总工,此时正在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省化工厅厅长何世镛的陪同下,沿珠江驱车来到这里。
他们刚从北京到上海,看了吴泾化工厂的建设,又到了衢化。两家氮肥工程,摽着劲儿干,打得很苦,但都很顺利。已临近春节了,他们仍无回京念头。这一站又来到广州,看看广州氮肥厂的建设。这几年,吴泾、衢化、广氮,吴亮平是穿梭般往来,扎到哪家,一住便是一个月20天的。这三个厂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已制造设备,自己组织安装,自己组织安排生产的第一批2.5万吨氮肥企业,可谓20世纪60年代初化肥建设中的“天之骄子”。每次,他都带几个经验丰富的化工专家,指导建设,指导安装,帮助解决问题。
此刻,他们要去珠江二沙头畔的一座小楼,拜访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陶铸的眼里,那可谓“广氮是广东的宝贝蛋”,从国务院、化工部决定把一座年产2.5万吨的合成氨、10万吨硫铵的化肥项目放在广州,陶铸便把它放在了心里。他常被近几年广州人的“逃港”现象搞得十分恼火。他发誓,共产党既能把老百姓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更能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幸福美满的好日子。首先得让人民吃饱。要吃饱,没有化肥不成。现在,广东也要建设第一座这么大的化肥厂,他能不高兴吗?
1957年一立项,陶铸立即调兵遣将,摆下最强有力的干部阵容:省工交部部长刘田夫任筹建处主任,陶铸的夫人、广州市委书记曾志,市长焦林义,副市长孙乐宜任副主任。
1959年春夏之交,广东省化工厅长何世镛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去汕头参加省委常委会。他愕然。“是不是通知错了!”他打电话询问。省委办公室这回更干脆:“没错儿,是陶铸同志点名让你参加的,专谈化肥问题。”
广州市一大半基建队伍都上了广氮。广氮进入安装高潮。1961年夏季的一天,厂技术监督科科长陈家文到工地检查安装质量。高压设备合成塔,是他格外瞩目的目标,这家伙弄不好,可是个大炸弹,一点儿马虎不得。突然,他在塔内壁见到一条细纹,不由得一惊。打开手电细照照,用手细摸摸,可了不得,真是一条裂纹。他赶紧汇报给总工程师张炳驹。
张炳驹一听也是大吃一惊。他知道这是东欧进口的设备,如真有问题,谈判,鉴定,索赔,更换,可是件大麻烦事。然而,就是再麻烦,也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他虽已年过半百,仍领着几个小伙子钻进合成塔,用砂纸、砂轮打磨,试验。真是有条裂纹。测定了长度、深度,立即向部里作了汇报。请来东欧一位当了多年化工厂厂长的专家鉴定,对方仍不明确表态,谈判艰难。
世界知名化工专家侯德榜听到此事,立即来到广州。72岁高龄的他,亲自钻进合成塔,作出了鉴定,对方无话可说,同意赔款。接着,侯老决定合成塔由首创我国第一台高压容器、经验丰富的南化机械厂承制。
中央与地方齐心协力办化工、办化肥,使广氮如羊城花市一般掀起新的建设热潮。焊花比鲜花艳,锤声比爆竹响。1963年3月4日,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等亲自为广州氮肥厂造气炉点火。4月22日,第一袋完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化肥冲出了运输线。至此,吴泾、衢化、广氮全部投入运行。历经千辛万苦,中国氮肥工业终于开始大片灿烂辉煌。
责任编辑:陈尔东
znchenerd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