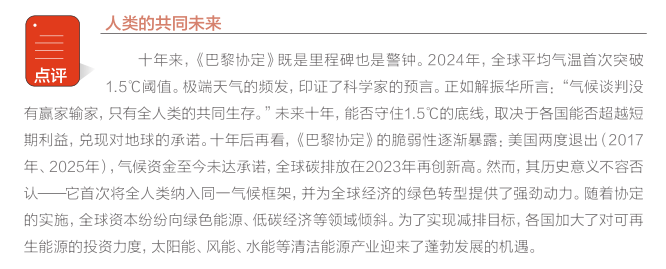- 最大
- 较大
- 默认
- 较小
- 最小
十年前巴黎那场鏖战,首次将全人类纳入同一气候框架。
2015年,一场牵动人心的谈判在巴黎举行。最终,在巴黎北郊勒布尔歇展览中心,当着195国代表的面,时任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敲下绿色木槌,宣布《巴黎协定》通过。现场代表起立鼓掌,许多人热泪盈眶。如今十年过去了,再重看那一幕,依然能体会到当时的暗流涌动。
哥本哈根阴影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繁;洪灾和干旱频频发生;部分生物将灭亡,人类的食物出现短缺……
这样的画面,是科学家向我们描述的地球升温后的景象。
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会导致地球升温。2015年,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地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了约1℃。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发出警告:若升温超过1.5℃,其国土将被海水淹没。与此同时,科学界达成共识:将升温控制在2℃以内是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底线,1.5℃则是更安全的目标。
为了控制地球升温,1995年,在柏林举行了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然而,全球近200个国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1997年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只有发达国家有减排的法律义务。但美国因为国会不同意而退出,加拿大、日本也相继退出。尽管这是第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减排协定,但其效果相当微弱。
2009年,多数国家决定在哥本哈根签订一份包含所有国家的减排协议。尽管人们对其报以厚望,但一个“从上而下”让各国“分配”减排指标的体系,必然会遭到抵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相指责,参与国的代表怀着满心愤怒和失望离开。
“哥本哈根的失败,让最坚定乐观的人感到脊骨发凉。”6年后,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德回忆说。
2011年的南非德班,在艰难谈判后,各国终于同意于2015年在巴黎“重做哥本哈根的功课”,签订从2020年起生效的全球减排协议。然而,“哥本哈根的阴影”依然存在。届时能否实现目标,不得而知。
939处分歧
无可否认,巴黎谈判是一场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的角力。
“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任何全球性减排协议都没有意义。”这是与会各方早就达成的共识。然而,在当时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变化”是个遥远的话题。
发展中国家认为,当年依靠化石燃料实现富裕的发达国家,必须继续肩负减排、出资等责任。“其他安排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印度总理莫迪在《金融时报》的文章中称。
发达国家则尽全力希望废除《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他们认为,所有国家应该遵循同一体系的标准,尽管可以根据各国能力情况给予“灵活性”。
2015年11月30日,在巴黎北郊勒布尔歇展览中心,会场内的气氛更加剑拔弩张,来自195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
巴黎大会开幕当天,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等150位国家元首到场,规模空前。
谈判第一周过去后,草案文本仍有多达939处未有共识。
谈判进入第二周,许多会议开始采取闭门形式,信息密不透风。
谈判桌上,各国利益的博弈比气候本身更复杂。美国因国内政治压力,坚持“自愿减排”模式,以避免国会否决;欧盟则要求协议必须具有法律约束力;发展中国家则高举“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大旗,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
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低碳还是无碳?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最迟在2050年完全停止使用石化燃料,但很多国家希望本世纪内只向低碳经济转移。
谁出资金?2020年,发达国家能否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在巴黎协议资金条款中使用模糊的语言表述,并希望发展中国家承担出资义务。
如何审核?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希望制定一个可测量、可汇报、可核实的审核机制。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具有侵入性的审核机制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
《巴黎协定》第六条关于国际碳市场的设计,因牵扯数万亿美元利益,成为技术谈判的“黑洞”。巴西坚持要求允许重复计算碳信用(一国减排量既算作本国贡献,又可出售给他国),遭欧盟激烈反对。
…………
近200个国家,近1000处分歧,能否达成一致?大家拭目以待。
落下绿色小锤
2015年12月12日,经过近两周的极限拉扯,各国终于通过了《巴黎协定》的最终版本。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出席并讲话。“历史就在此刻,我们现在只差一步。”奥朗德说。一小时后,由法国作为主席国亲自拟定的协议文本,在会场上发给大家。
协议文本达成了一个最核心的目标:协议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从2023年开始,每5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
这是继生效约二十年,并将在2020年“退役”的《京都议定书》之后,全球签署的第二份控制气候变化的重要约束性协议。
这其中,包括最为引人注目的“阳光条款”:所有国家都要对减排和资金情况进行汇报;各国要定期提供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等信息;所有国家将遵循“衡量、报告和核实”的同一体系,但会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提供灵活性;对提供资金和减排情况,会有第三方的技术专家审评。
下午5时30分,能坐数千人的大会场已经满满当当的。但直到7时15分,满面疲惫的时任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才坐上主席台。
“《巴黎协定》通过了。”法比尤斯敲下手中那个绿色的小木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木槌,但它能做伟大的事情。”现场代表起立鼓掌,许多人热泪盈眶。后来,法比尤斯回忆说:“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仍在说服犹豫的国家。”
自此,全球气候治理的完成了范式转变。《巴黎协定》摒弃了《京都议定书》的“自上而下”模式,采用“自下而上”的NDC机制,兼顾灵活性与集体行动目标。截至2016年4月22日开放签署首日,175个国家签署协定,创下了国际协议单日签署数纪录。2016年11月4日,协定正式生效,比原计划提前4年。
责任编辑:赵 玥